一、社会事实
法兰西是一个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尽管信教在今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盛行
[1]。在法国存在着“六大宗教”,其信仰者包括75万新教徒,65万犹太教徒,20万东正教徒,以及600万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
各个新教教会并非一个单一的、一体化机构的一部分,但它们共享一种特定的“相互关联”的结构。在每一个堂区(parish)内,由堂区协会选举出一个堂区委员会。众堂区被编组成为“团”或“路”(“consistories” [circuits]),每一“团”或“路”,由该地区所有在职牧师,以及两倍数量的平信徒代表构成。在更高层级,组织架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这里仅提及两个最大的教会(组织):归正宗教会(the Reformed Churches),该教会拥有数量最多的法国新教徒,设有地区宗教会议(synod)和全国宗教会议;位于阿尔萨斯和摩泽尔的奥格斯堡宣言诸教会(the Churches of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in
Alsace and Moselle),它们设有督导牧师团,以及高等宗教法院(the Higher Consistory)。在1905年法案之后,曾依照1901年法案设立法兰西新教联合会,在较长时间内,它都是一种教会联合会,其中的每一家教会都希望自己能独立于其他教会。法兰西新教联合会仅能以成员一致投票通过的方式形成决议,这表现了一种深刻的互相不信任。1962年通过的新法规,使得该机构获得了一种新的面貌,此后,该机构能够以多数表决的形式通过决议(除了在教义方面)。尽管该联合会并不包括所有新教团体,但在联合会的目标当中,也包括“在与政府当局、外国和国际机构的关系中,代表法兰西新教”这一条。还有一些机构,它们只有与世俗团体合作才能运行,这些机构也是该结构的一部分(如在信息机构、青年群体、外联、广播电视、监狱中行使牧职……)。
(法国)犹太教拥有类似的结构,包括等级分明的治理机关。中央宗教法庭(the central consistory)设于巴黎,从所有犹太宗教团体中产生形成,它作为法兰西犹太教的代表机关,与国家当局打交道,并且,它选举法兰西首席拉比。“法兰西犹太组织代表委员会”(the Representative Council of French Jewish Institutions)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伊斯兰教将来自各种不同背景和国籍的人们联合起来,但80%居住在法国的穆斯林是层次较低的劳工。他们分属不同的宗教组织,这导致协调行动的困难。内政部中的宗教局(the Bureau des Cultes)负责与他们打交道。2002年4月,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French Council of Muslim Cult)以及地区分会,由众清真寺选举出来。穆斯林拥有大量崇拜场所,但这些场所境况困难、资源匮乏。在法国,如果仅仅从建筑的意义上使用该词汇,那么,只有八个“清真寺”。
东正教诸教区,以族群或民族为基础组织起来,由跨教区委员会(the Inter-episcopal Committee)协调,该委员会由代表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的都大主教(the Metropolitan)主持。
最后,佛教徒联合会(the Union of Buddhists)涵盖了80%的声称追随佛教传统的庙宇(pagodas)、中心、团体。
二、历史背景
在法国,教会的法律地位严重依赖于历史。
1. 1789年8月26日,《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告了“信仰自由”(第10条),1791年的宪法(第一章)确保宗教自由。1789年11月2号的法令,开启了针对教士财产的国有化;作为回报,国家承诺负担教会的运行成本,以及神职人员的生活费。(1790年7月12日)《神职人员民事宪章》(the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一个由国家单方面颁布的法规,规定了宗教神职人员的地位以及天主教信仰活动的组织形式。依照该法规,教会从属于国家,并被当作一种公共服务机构来对待。庇护六世〖于1791年3月10日,在一份教廷通牒Quod Aliquantum中)〗谴责了该宪章。更进一步,国民公会——尤其是在恐怖时期(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通过了一项系统的去天主教化的政策。1795年2月21日的法令,确立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制度;尽管宗教活动自由被得到确认,但共和国并不提供任何薪水和任何地产,也不承认任何宗教神职人员。教会受到严重迫害。
2. 经过谈判,拿破仑与庇护六世于1801年7月15日(法国共和历10月26日)签署协议,以此恢复了宗教和平。在第十七条的简短文本中,拿破仑留下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内容
[2]。协议被“组织条款”(77条)加以完善,这是一个法国政府的单方面的法案,从未被罗马接受,但其与协议同时于1802年颁布(法国共和历7月18日法案)。在十九世纪中,其后的历届政府都推行了该法案。这些“组织条款”(Organic Articles)确立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允许世俗当局对宗教神职人员以及宗教生活的开展实施严格的控制。在该法以外,拿破仑又增加了44条与新教教会有关的“组织条款”,迫使归正宗教会和奥格斯堡宣言教会在组织上接受管控措施,这些措施类似于适用于天主教会的措施。犹太教则根据1808年的三个法令被组织起来。
其他的文本进一步完善了这些法律规定,阐明了宗教神职人员的合法地位,他们的薪水,以及适用于被划归教会使用的财产的法律规定。某些公共宗教团体管理这些遗产;尤其是那些结构和权力被1809年12月30日的法令所规定了的团体。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四个“被承认的教会”享受着特定的优待,尤其是财务上的好处,但它们也受到政府当局持续不断的监控。
上述这些立法,曾在各种极其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被推行。优待或者敌视天主教会乃至所有宗教的政府频繁更替。在19世纪,法国跟其他地方一样,宗教利益是所有政府中基本的政策争论的要害部分。法国大革命为后来的冲突预设了伏笔,自1830年“七月王朝”开始,在天主教会内部以及政界中,不同的意见倾向导致两个对立集团的形成。一派由传统秩序的拥趸构成,他们所关心的是古老政体的复兴,被视为教士权力的无条件支持者。另一派,新秩序的拥护者,他们追随1789年的价值观,是天主教及其教士团体的无情反对者。在两个对立派别的简单画面背后,可以发现更为复杂的情形。但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潮流,使得教会的法律地位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一项政治争议。在1879-1880年之后,共和党人一度又获得政权,反教士主义(anticlericalism)遂成为他们的政治行动中的头等要务。对他们而言,共和政权的存在本身,是与一个葆有活力的教会不相兼容的。由于头脑中的这一信念,他们通过了19世纪80年代的诸多反教士法案,这些法案对教会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这些法案中的大多数今天依然有效。1904年,法国与教廷的外交关系中断后,1905年12月9日的法案确立了法兰西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制度。
3.1905年法律的前两条确立了关于教会的新地位的基本原则。共和国确保公共礼拜活动的自由,但废除了“被承认的教会”的地位。法律上不再立教。教会不再是公共机构,而且必须成为私人领域之一部分。经过一定的拖延,教皇在(1906年2月11日)通谕中谴责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并要求主教团反对1905年法案的实施。有一些较晚出台的法律试图弥补由于天主教会拒绝合作所造成的法律空白。
1870年,法兰西东部的三个省(上莱茵、下莱茵、摩泽尔)被划归德国统治。德国皇帝与教廷同意,在合并时保留法国的宗教法规在斯特拉斯堡和梅斯教区的效力。帝国的法令更改或补充了某些规定。在上述三省于1918年回归法兰西后,政治领袖以及当地人民希望保持现状。阿尔萨斯和摩泽尔的当地法规保留了“被承认的教会”(Recognized Churches)的制度,由国家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05年的法律不适用于它们。
三、法源和宪法制度
基本原则被载入1905年法律。事实上,1958年的宪法并未修正有关教会的宪法制度,仅包含两个涉及教会地位的条款
[3]。宪法中的这些法律来源虽然贫乏,但起到了基本的作用,因为它们确立了国家中立这一制度。1905年的法律在其开头的两个条款中提出了基本原则:宗教活动自由,但是不“承认”(recognition)、不资助
[4]。
当代“法兰西世俗主义”(French Laicite)的理念规定了“积极中立”制度。依据这一制度,信仰自由的原则给国家施加了积极的责任,以适应政教分离的制度。国家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出席他所属教会的仪式,所受到的信仰指导对其所选择的宗教来说应当是恰当的。渐渐地,在法兰西,一种新的关于国家角色的理解流行开来,它要求:国家应时常干预,以便对每一种宗教的公共崇拜活动而言,其在任何地方实际所需的必要条件都得以具备。
不同宗教之间的平等意味着,不存在国教,不存在“官方的”或主导性的宗教,不存在“被承认的教会”……没有任何宗教拥有特殊的公共地位。1905年的立法者想要使宗教成为一项私人事务,并作为私人事务受私法支配。但是,国家并不总是将宗教当作纯粹私人的,有时它又授予宗教一种不同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特殊体制适用于何种团体或何种活动?什么是宗教?问题是复杂的;立法者,法庭和理论家并没有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国家中立,不“承认”任何宗教,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给出答案。实际上,是法官(国务院或最高上诉法院)在对各个案例逐一做出裁决,同时,避免给出一个在其他案例中可以作为救命稻草被付诸应用的一般的定义。因此,针对每一个团体或协会,是否应承认其具备教会的特征,是否那些对宗教团体具备效力的有利或不利的法律规定也适用于它们,法庭只能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做出裁决。宪法的缄默,政教分离的体制,国家的中立,以及立法者的审慎,使得法兰西的教会法(ecclesiastical law)主要源自法官的裁决。诚然,在法国存在着法律、法令以及其他规定。但法兰西需要在应用过程中更具备弹性和准确性的法律来源。法律、法令或规定有两种形式:内政部宗教局所颁发的部颁文件,以及大量的国务院、最高上诉法院,还有——晚近以来以及在较低程度上的——宪法委员会的案例法。
四、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新兴宗教运动的处境
尽管有不承认教会这一原则,但在法国的法律系统中,宗教依然受制于一些特别法规。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授予教会某种地位,而是一些适用于一系列组织、机构或团体的法规对于教会的存续而言非常重要。这里,我们要提及若干重要案例。我们需要指出,还有很多其他团体(基金会、教会公司等)和法律原则,本文就不涉及了。
1. 宗教协会(Religious Associations [associations cultuelles])
1905年法案第4条对“宗教协会”的成立作了规定,宗教协会可以获得在1905年受到压迫的以前的公立教会机构的财产。相关的协会受1901年7月1日法律的支配,该法律管辖所有的协会
[6],而且,相关协会须符合1905年法律中所设定的某些附加规定:第19条要求它们必须“完全为了教会的目标”;它们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国家、部门或市镇的补助金”。法律还规定了社团的必要构成,以及与当地人口有关的社团规模。也对被许可的资金来源做了规定:它们必须总是由信徒提供,但那些为了维修已登记在册的纪念物而收集的款项除外,后者不会被当作“补助金”(subventions)而被禁止
[7]。这些宗教协会已越来越从税法所规定的优惠政策中获益,这意味着,宗教这一“标签”现在颇受欢迎。1905年以来,根据1905年法律的所有规定,新教教徒和犹太教徒借助于法律成立了宗教协会,这些协会直至今天仍保持活跃。
2. 教区协会[Diocesan Associations(associations diocesaines)]
在谈到宗教协会时,我们还没有提及天主教会。这种缄默是有意义的。天主教会拒绝实施1905年的法律,因为教廷反对,并且主教团中的一部分人关切“宗教协会”这一问题。天主教的等级制度使得它害怕大量的、不同的协会出现,这些协会可能都声称属于天主教会,但等级制度又控制不了它们,而且平信徒在这些协会中有可能拥有决策权。当这项法律还处在审议过程中时,法兰西教会中的很多人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而且,他们的意见在国会辩论中也得到了呼应。最终,该法律第4条规定:宗教协会必须符合“协会所归依之宗教的一般组织原则”。这一表述没有提及天主教会,但天主教会的等级体系仍有望继续保留其权威。虽然有这一保证,但天主教会并未建立任何宗教协会。为填补法律空白,1907年1月2日的法律规定:公共宗教活动,可由符合1901年法律的协会举办;亦可依照1881年关于公共集会自由的法律,通过个人发起的集会来开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看上去获得了改善。法国与教廷的外交关系被重新建立起来;同样,经过长期谈判,法国与教廷达成了协议,天主教会可按照一系列特别模式的规定设立教区协会。国务院承认,这一特殊地位符合法兰西法律,尤其是1901年和1905年的法律(国务院意见,1923年12月13日),并且,庇护十一世也授权,可以成立协会(教皇通谕,1924年1月18日)。自1924年起,法兰西的主教们设立了教区协会,这些协会是宗教协会,符合1901年和1905年的法律,即便“承担教会支出”不再作为这类协会的“专门的”目标而被提及。教会法的诸原则也得到遵从,协会的行动“按照主教的权威,与教廷保持一致,并遵守天主教会的章程”[模范法规(the model statutes)第二条]。
这一发展给天主教的法律地位带来影响,因为新的实体的目标是组织宗教活动以及管理用于宗教活动的财产。相应地,关于教会建筑的所有权这一问题,根据1905年法律,新教和犹太教会的建筑均被交付相关的宗教协会。另一方面,1907年1月2日和1908年4月3日的法律却将现存的天主教会的建筑所有权,以及维修的责任,转交给国家(主教座堂以及主教官邸交由中央政府;堂区的教堂以及堂区神甫宅邸归市镇政府)。与之相反的是,1924年以后,教区协会负责决定并兴资建设新的崇拜场所,并作为主人确保其得到良好维修。
这些历史的变迁诠释着几种协会的共存:1905年法律管辖下的宗教协会(associations cultuelles);由1907年法律条款规制的以教会为目的的协会,这种协会遵从1901年法律的规定;还有教区协会,它们遵从1901和1905年的法律,但又服从额外的标准。另外,1901年法律所规定的结社自由准许大量协会的发展,尤其是以慈善和教育为目的的协会,它们与宗教权威当局协同工作,但并非以宗教为专门目标,因此,它们并不是“宗教的”(cultuelles)。在上述这一类别中,主要包括众多带有宗教色彩的、以教育为目标的文化协会。穆斯林现在利用了1901年法律中的这一合法形式:一间古兰经学校的存在,为使其获得正当资格,可被称为“文化的”(cultural),尽管事实上在学校以外还有清真寺,由同一个“文化协会”(cultural association)管理。宗教意义上的协会与文化意义上的协会之间的区别,反映着一种本质上的法律差别:前者由1905年法律管辖,后者由1901年法律管辖。它们的财务和财政体制各有不同。
法国的法律条文没有界定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 (religious order)]这一术语,因为1901年立法者的首要目标是将修会从国家领土中清除出去。当人们希望彻底把某种组织扫地出门时,他们不太会费心力给这种组织下定义。何种群体可以被划入宗教团体的范畴,这一任务落到了法官的头上。某些实际情形会被纳入考量的范围:宗教誓约的存在,修会所从事的虔诚的事工,修会成员对宗教权威方面所认可的成文法规的服从……
宗教修会目前的地位最好也是通过历史来解读。十九世纪的立法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一般而言,要批准一个宗教修会,需要一部法律或法令的授权。然而,大多数修会的存在,都没有在良好和恰当的形式上获得这样的授权。在第三共和国统治下,宗教修会不得不消失。在这种意义上,1901年法律的第三章宣布取缔任何未获得合法承认的宗教修会
[U1] (第13条)。并且,国会系统地拒绝任何由宗教修会所提出的给予承认的请求。但是,自1914年起,未经许可的宗教修会回到了法兰西;他们是非法的,但未受到迫害。1942年4月8日的法律改善了他们的地位,因为该法取消了“非法团体”这项罪名。没有法律上的存在,或没有法人资格,他们仍可以作为事实上的团体而存在。另一方面,授予合法承认的程序被简化了:“授权”(authorization)变成了简单的“法律承认”(legal recognition),通过国务院令以及授予法律能力来施行。不过,只是在1970年以后,这一程序才影响到新的修会,1987年以后,这一进程加速。
1987年,法律承认的程序向非天主教修会开放
[9]。一个被承认的宗教修会,拥有完全的民事资格:在法兰西法律管辖下,其地位接近于那些被承认的、具备公益性质的协会(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宗教修会就是一个协会)。宗教修会必须接受国家的一种信托形式的监督,近来,这类监管措施已经明显地放松了。
4. 新兴宗教运动和“教派”(sect)
由于拒绝界定宗教,法兰西的法律在处理新兴宗教运动时,面临一些困难。但是,诸审议庭,首先是国务院,并未将每一个自认为是宗教组织的团体承认为是“宗教”的团体。假如政府当局承认,一个宗教运动按“宗教协会”的形式自我组织起来,那么,这一事实本身意味着,当局承认,该宗教运动属于一种宗教,即使当局自己绝对不使用该术语。“宗教协会”这一范畴很少被用到,尤其当涉及新兴宗教运动时。法庭不愿意说一个团体是否是“宗教的”(religious),因此他们不愿意承认一个协会是宗教性的。有些“教派”曾试图按照1905年的法律,以宗教协会(associations cultuelles)的形式,将自己组织起来;对此,国务院总是不予许可,根据是,1905年法律第19条强调,宗教协会必须以宗教为专属目标。在每一个案例中,据认为,相应协会的目标都似乎与公共秩序的维持不相兼容,或者该协会有其他形式的活动(文化的、商业的、医疗的……)。
如何在“宗教”与“教派”之间作出区分?长期以来,法兰西的立法者以宗教和良心自由为名,拒绝就“教派”进行立法。针对这些新兴宗教运动的斗争,主要是法官们的工作,法官们拒绝给予新兴宗教运动财政上的优惠,而“宗教协会”享有这些优惠,法官们还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2001年6月12日的法律引入了多种不同的手段,以便控制“教派性活动”(sectarian dealings)。法官可以解散一个法人,如果其行为带有危险性。法人刑事责任方面的制度已被扩充。法律设置了一项罪名:“滥用他人无知状态或弱势情形的欺诈”。那些被认可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协会,在反对教派方面可以成为诉讼程序中的一方。
各大宗教已表明它们的关切:政府当局在实施这一新法的时候,不应限制宗教的自由。
教会提供广泛援助,并通过“特殊”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它们与政府合作,兴办具有宗教色彩的机构,尤其是在教育(参见本章第六节)以及援助领域。
在法兰西,援助和医疗关怀主要是国家的服务项目,与其他欧洲国家(例如德国、荷兰)相比尤其如此
[11]。然而,提供关怀是教会工作的核心部分。法国法律准许教会掌控它们自己的服务机构,无论这些机构提供的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医疗服务。这主要指的是在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主教会。
从国家法律的观点来看,以宗教为动因的慈善工作并不因其信仰特征之故而拥有某种特殊且一致的法律架构。它们像任何其他私人机构一样运行。具有宗教特征的私立医院,可以是基金会,由国务院法令宣布其公益的性质;或者是公司;或者采取协会的模式,属于下面两种协会形式中的一种:根据1901年法律具备法人资格的协会;以及被承认属于公益、具备扩大的法人资格、能够接受馈赠和遗产,但是须接受更高程度的行政监管的协会。其是否被承认属于公益性的,并不取决于其信仰特征,而是取决于其相关事务中所追求和达到的社会目标。
政府并不反对某些这类活动中的信仰特征,并且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考虑范围,尽管这些信仰特征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法律地位。人道主义援助
[12]和医院工作
[13]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可以大不相同。宗教团体、公司、或者是兴办特定机构的协会,它们可以拥有也可以不拥有建筑物、建筑物下面的土地以及设施……它们可以依赖于私人基金、宗教团体的财产、基金会、捐赠以及募集……来自国家或地方当局的公共基金中的补助金额,将会加入这些资源之中,因为这些拨款不会被看作是对教会的补助金——这是为1905年的法律所禁止的——而是被视为对公益工作的支持。
教会当局(ecclesiastical authorities)可以授权或禁止具有“独特特征”的机构中的某些医疗措施
[14]。他们对宗教医院中的工作人员拥有控制权。在医院中工作的修士与修女仍依赖于其宗教修会而非医院。如果有聘用合同的话,是在该机构与宗教修会之间签订;修士与修女并非合同中的个人一方。在有宗教背景的医院中,平信徒越来越占多数。他们的法律地位(招募条件、工作条件、以及授权……)取决于世俗法律以及现存的集体谈判机制。聘用的资格取决于国家颁发的文凭。但是,教会当局可以将他们自己的要求加诸于雇员,而民事法官对此会予以尊重
[15]。这些额外要求与某些重要问题有关,但其非常具体,且数量很少。任何未被宗教当局以这种特别方式处理或对待的,普通聘用法规将适用。
五、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在法国的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体制下,诸宗教派别原则上不拥有任何直接的、被官方认可的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重大的社会争议,尤其是在伦理问题中,政府常常咨询主要宗教派别的代表意见。另一方面,存在着几种与宗教有关的法律制度,它们都以世俗主义为基础。不过,1905年的法律仅仅只在大都会地区施行,并未及于整个领土范围。
在法兰西东部的三个省(上莱茵、下莱茵、摩泽尔),有一种“被承认的信仰”(recognized cults)体制,由拿破仑体制继承而来,在1871至1918年期间,被德国立法修订过,1918年阿尔萨斯和摩泽尔回归法国后,在某些方面又获得了修正
[16]。隶属于该信仰组织的神职人员,其薪资由国家支付;公立学校设有宗教课;斯特拉斯堡的大主教和梅斯的主教由国家首脑任命……
一些海外的省或领地也有一种特别的体制。1905年的法律并未在三个省(留尼旺、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实施,协约体制在十九世纪初即已被引入这些地区。法属圭亚那由1828年8月27日的皇家法令管辖,根据该法令,天主教由公共资金予以资助。1939年的“曼德尔法令”准许其它宗教享有特定权利,首先是可以获得当地社区重要的财务援助。这些法规在大多数海外省份或领地实施,但是,其伴随着许多具体的规定。
[17]
六、文化领域:私立学校—宗教教育—公立大学中的神学院—媒体
自1848年宪法(第9条)以来,教育自由是一直被确保的一条宪政原则。尽管最近的宪法文本(1946年和1958年的宪法)并未明确提及该项自由,宪法委员会在两项裁决中仍然确认:教育自由是“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之一”
[19]。
教育自由系由十九世纪的一系列法律管辖,这些法律中的每一部都是起草于教会与国家的政治关系进程中的某一个特殊阶段。这种特殊的历史,可以用来解释私立学校——根据其各不相同的教育层次——组织和财务制度的多样性,以及教会在不同层级的公立教育系统中所拥有的地位的多样性。
[20]
确立教育自由的法律文本目前原则上仍保持有效。它们准许创立一个“自由”的教育部门,该部门与1806年拿破仑所设立的大公共服务部门比邻而立,该部门在教育系统拥有绝对垄断地位
[21]。今天,在所有的学生当中,差不多18%就读于私立教育体系。90%的私立教育机构是天主教会的,其余10%包括新教和犹太教学校,以及一小部分非宗教性学校。这类私立教育被看作是国家教育服务体系当中的一部分
[22]。通过德勃雷法案(
loi Debre)(1959年12月31日的法律),私立教育——宗教或非宗教的——获得完全承认;其“独特的特征”被确保。私立(教育)机构可以与国家订立一种合同制的关系,正如绝大多数案例中的情形
[23]。
私立的宗教学校提供宗教教育。但是,那些与国家签订合约的学校,他们承诺,在接收学生时,不分种族和宗教;在那里,宗教教育并非必修。
2. 公立学校中的宗教教育——机构中的牧职 [
aumoneries ( chaplaincies)]
[24]因为历史的原因,除了法兰西东部三省,公立教育都是世俗的,但是,根据所涉教育的层次,世俗主义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形式。以下是目前的情况:
关于小学,1882年3月28日的法律——那一时期共和派政纲的主要构成部分规定:学校每星期必须留下完整的一天,以便家长——如果他们希望如此——安排学校之外的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可以不在学校内进行。学校提供“道德和文明”课程,而不是“道德和宗教”课程。实际上,上小学的孩子星期三没有课程
[25]。
- 就中级学校而言,当拿破仑为男性儿童创建公立中学(lycees)时,他设立了校牧[aumoneries(chaplaincies)]的职位,作为学校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1880年,卡米尔·西法案(loi Camille See)为女性儿童创设了公立中学(lycees),并安排了教会教师,但其不作为学校的一部分,与男校中的牧师自世纪初即已开始享有的地位相比,其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 第三共和国废除了教会教师。1905年以后,校牧可以存在;但国家没有责任负担其薪酬,而且也没有这样做过。多种法律文本(1960年4月22日的法令,1960年8月8日的命令,以及1988年4月22日的部颁文件)管辖此事。校牧职位由学校校长根据家长们的请求设立,并且,其行使职责有时在校内,有时在校外。其薪酬的一部分由家长的捐款支付,一部分由教区支付。实际上,校牧由校长根据相关宗教当局的提名任命。
依据阿尔萨斯-洛林的当地法律,在法兰西东部三省,宗教教育原则上被保留下来,就如同由1871年以前具备效力的法律管辖时的那样。在公立学校中,包括小学和中学,宗教教育都是总体课程的一部分,教师原则上由国家支付工资(尽管事实上小学经常要寻求捐款)。一个家庭拥有相当的自由,来决定孩子是否应参加这些课程。该类课程的成绩不计入学生的评估之中。
在国立大学中,教育是世俗的;这导致19世纪末宗教课程几乎消失不见。教会史在人文学院仍保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法学院中,涉及教会的法律只被给予很小的空间;教会法典(Canon Law)仅在法制史的语境中被触及。“教会法”(Ecclesiastical Law)不是任何课程的主题,而且,仅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被某些公法教师在宪法或行政法的语境中提及,或者在公共自由的语境中提及,以及被私法教师在与婚姻、与家庭,或与公共秩序(
ordre public)观念的关系中提及。
[27]
依据1875年7月12日法律之条款,一种“自由的”高等教育部门得以存在。1880年,在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的高峰,共和派禁止这些教育机构使用“大学”的称号。它们所授予的是自己的毕业证书,而非国家的证书。不过,自1970年以后,在国立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已存在众多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自由”部门的学生,可以经由联合考官委员会(由来自两种教育机构的教师构成)的考试,同时获得国家的文凭以及私立教育机构的文凭。
[28]
教会拥有自己的新闻部门,并且可以通过公共或私人的世俗媒体,使其观点为世人所知。
教会拥有报纸、广播台,例如圣母电台(Radio North-Dam)以及专门的节目。就天主教来说,媒体工作是由一个实体来协调,该实体由主教团秘书处创办,名为“全国基督徒媒体”(Chretiens-medias National)。天主教新闻界拥有很大的发行量,包括日报(La Croix)、周刊(La Vie, Temoignage Chretien…)、以及专门的出版社(Bayard Presse…)。另外,“法兰西基督徒广播联合会”(Federation française des radios chretiennes)的管理委员会包括“新教联合会”(Federation protestante)、天主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the Armenien Apostolic Church)以及东正教会;该联合会拥有30家电台。
世俗媒体也提供一部分空间给宗教问题,并听取教会人士的意见。这一任务部分地由国家的广播和电视台来负责。二战以后,创办了“主之日”[“
le jour du Seigneur”(the day of the Lord)]电视节目。一个国家广播网中现在每个星期天都有专门的节目段留给法兰西的每一种主要宗教
[30]。根据1886年9月30日法律之第56条,这种实践是公共服务的一项责任。
1946年宪法的“前言”——1958年宪法提到了该“前言”——其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出身、见解或信仰之故而在工作或雇佣中被歧视”。那么,宗教信念,或者甚至是教会中的牧职,对劳动法没有任何影响吗?实际情况较为微妙,而且,每人立场各有差异,这取决于相关个体曾被授予神职,或者只是平信徒。
1. 法兰西劳动法与宗教神职人员
从原则上讲,教会中的地位在法兰西法律中没有任何民事上的影响。在考虑一份雇佣合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时,它无关紧要。当一个非宗教性雇主招募雇员时,应聘者没有任何义务声明其信仰情况;案例法已判定,基于未能透漏信仰状态这一事实而被免职,是不恰当的
[32]。这就是劳动法关于“工作者-教士”(worker-priests)的处置方式。
对于发挥着牧养作用的宗教神职人员(ministers of religion),例如堂区的教士或牧师,存在着不同的考虑。神职人员属等级制度中上级的雇员吗?还是宗教协会或教区协会的雇员?或者是给他委派职责的某机构(个体或者是具备法律人格的实体)的雇员?或者是给他发放薪金的某机构的雇员?自1912年最高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以后,案例法一直是非常一致的。在教士与其上级之间,不存在雇佣合约;前者并非后者的“雇员”。他们的关系属于一种不同的类型,世俗法律保持中立,拒绝就教会内部机构所产生的关系进行分类。因此,当一位主教决定暂停一位教士或者修士在教会中的职责,此举可能导致其最终被开除,民事法庭的立场是,无能力就此做出评判。
但是,宗教神职人员也拥有某些被雇佣者的权利,包括那些与国家的保险有关的权利。从1945年社会保险体系被启用以来,新教的牧师和犹太教的拉比即从中受益。关于天主教的教士和修士,1959年之后,负责医疗的特殊社会保险机构建立起来,然后负责退休事宜的特殊社会保险机构也建立起来。其越来越接近于一般社会保险体系的管理。最终,通过1978年1月2日的法律,天主教教士被纳入社会保险之中,但是他们所享受的待遇颇为有限(with a limited régime)。
[33]
2. 法兰西劳动法与在宗教环境中工作的俗人
在教会中工作的普通人员(lay people或译“世俗人士”),其地位各异
[34]。他们可以履行世俗的任务,或者加入教会的宗教团事工,帮助宗教神职人员发挥其牧养职能,就像“教牧工人”(pastoral workers)所做的那样。
普通劳动法适用于所有这些世俗人士,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侧重点。在教会实体中工作的俗人一般而言都有一份雇佣合同。雇佣者既可以是宗教协会(association cultuelle),也可以是教区协会(association diocesaine)。在法兰西法律中,堂区(parish)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作为雇佣方。雇佣者也可以是——根据1901年的法律——一个与一家教会有关联的协会。雇佣者与被雇者之间的关系,适用劳动法的一般法规。
但是,当世俗人士负担牧养职能时,教会可以施加额外条款吗?教区的主教给予每一个牧养工作者一份个人的“使命书”(lettre de mission),授权该牧工开展分配给他的工作,该授权常常是可以撤回的。只有拥有“使命书”,灵牧工作者才可以变成一个教区协会的雇员。那么,主教收回“使命书”是否意味着——根据事实——雇佣合同的终结?或者,雇佣方仍需要一份明确的解雇信?问题是,协会作为事实上的雇佣者,应该支付多少补偿。目前,正在讨论起草一种针对“教牧工人”(pastoral workers)的格式雇佣合同,这种合同应该考虑到主教颁发的许可证。
法院已经宣布,那些在天主教诊所或天主教私立学校工作的人士,如果他们离婚后又再婚,则解聘他们是合法的。这些雇员并不一定持有“使命书”(
lettre de mission),但他们确实在宗教性机构中工作。在相关案例法中,经过多次反复和曲折,最高上诉法院已裁定,一家天主教学校对一个离婚并已再婚的教师的免职,是恰当的
[35]。这一严格的判决并没有获得评论者的一致支持,它并不适用于那些在天主教诊所工作的人,这种诊所并没有学校那样的教育目标。
八、教会的财务
1. 历史总结
在旧的政治体制下,教会拥有大量的不动产,这使得其可以应付各项开支。通过1789年11月2日的法令,立宪会议决定,教士的财产国有化,并用出卖教士财产所得填补国库的赤字。作为回报,国家承诺给宗教神职人员提供充足的薪金。在政教协约时期(the period of the Concordat),国家和地方当局,尤其是市镇,持续地资助四家被承认的教会——其慷慨程度依时期而定,其中包括教士的津贴,房屋的建设、修缮,以及运行的成本,这一点是首要的。总而言之,这一体制今天在法兰西东部三省依然保持有效。
[36]1905年法律的第二条终止了教会的预算、神职人员的工资支付以及所有其他源自公共基金的补助。今天这依然是法律。但是,教会的持续困扰已经成为历史。教会现在拥有两个资金来源:一方面是私人的给予,另一方面是国家的间接帮助,这种帮助不等同于补助金。另外,那些并非“宗教协会”,但无论如何仍属于教会范畴的协会,它们可以接受公共的补助金。
2. 1905年以后的私人资金
这是常见的和基本的收入来源。现在,国家不再付给教士工资,几乎所有的教会资源都必须从私人源头寻找。每一家教会都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去募集资金,以及如何去运用它们。事实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办法;这里我们给一些例证:
在法兰西改归正宗教会,资金来自信徒的奉献
[37]。每一家当地教会自己管理自身的资源,但会以团结原则来减轻教区之间以及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的差距。牧师的薪金根据其年纪和家庭环境而有所不同,而非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
在天主教会,信徒的赠予同样必不可少
[38]。资源的使用及分配由教区这一级别决定。
赠与可以采用基金会的形式,这是一种不可收回的财产处理方式,适用于公共利益目标,可由一家教会实体创造和/或管理。
这分为四个类别:
某些宗教神职人员由国家支付工资,这并不违反1905年的法律。这些人是在监狱或医院工作的神职人员
[40],或者是私立学校中的教会教师——如果该学校根据1959年的法律与国家建立合同关系的话。
宗教协会或教区协会为建设新的礼拜场所而借的款项,国家可以为其做担保
[41]。出于同样的道理,自1930年起,出现了一种形式的抵押资助,由市镇给予宗教协会,一般以99年为期,每年支付一法郎的象征性租金。这种办法首先用于巴黎地区的教堂的建设,现在,它已经普及开来,并且未遇到行政上的反对。
第三 国家是1905年以前修建的天主教崇拜场所的拥有者。它承担主要的修缮任务。
最后,宗教协会和教区享受极为有利的税收制度。《一般税务法规》第238条准许企业或个体纳税者扣减其向公共利益服务机构工作的捐款,最高达一定额度。国务院在1962年5月15日的“意见”中,认定这一条适用于宗教协会,包括用于教会建筑的修建和维护的资金,或者用于特定的慈善、教育、社会或家庭性质工作的资金。但是,与此相反,1962年,用于支付宗教神职人员津贴的捐款,被认为不适用于“扣减”。
《赞助法》大大增加了有利于宗教协会的税务扣减的可能性
[42]。人们明白,各种团体在获得“宗教协会”这一标签后所能获得的好处;如我们曾经说过的,法官们对这种滥用保持着警惕。
4. 依据1901年法律而成立的协会的财务
某团体未能是“宗教协会”,却在教会领域工作,一般情况下,依据1901年法律,可以成立一家“协会”,从而被授权可向国家、地方当局以及其他公共实体申请补助金。这些协会只能接受个人的捐赠,捐款人不得享受税务豁免
[43]。那些被认定为具“实用性”(
utilité pratique)的协会,对它们的捐款可以享受税务豁免。
九、公共机构中的宗教援助
积极世俗主义的原则意味着国家确保每一个体拥有实践其宗教的相应手段。如果某一个体生活在一个由国家掌管的机构中,并且,不能到外面去参加宗教活动,他就应该被允许在该机构内实践其宗教信仰。因此,在人们无法离开的地方,国家承担进行精神援助的责任。1905年法律的第二条提出了“公立中学、学院、医院、监狱”。实际上,作为一种适用于这些非常不同的机构的制度,它是互有差异的,因为,和医院、监狱相比,一个人可以更容易地离开公立中学、学院
[44](即便作为住校生)。为了满足类似的需求,武装部队中也设立了军牧。
1. 医院和监狱
1905年的法律准许设立“随驻牧师”(chaplaincies)之机构,由公共资金开支,并且,针对此一目的,未设置任何约束。国务院的案例法,连同一系列部颁文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法律制度。
在医院,医院的院长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使住院者得以在院内实践其宗教。他必须做好医院内的相关部署。1976年7月26日的部颁文件则做出了更加确切的规定。医院管理方可以向不同教会的宗教神职人员求助,以帮助那些寻求心灵帮助的病人。在获得相关的宗教权威当局的许可后,这些牧师可与医院管理方订立合同。他们领取薪水,必须遵守医院的规章,并进入社保体制。他们的雇佣合约可因协议而不同,管理方在咨询相关的宗教权威当局后,可以提前三个月通知(严重行为失当者除外),单方面退出合约。
在监狱内,对囚犯的精神援助目前由1972年9月12日的法令规定。在咨询有资质的宗教权威当局后,司法部任命来自不同教会的牧师。被任命者并不持有合约,但其作为无编制的公务人员,受特别的规章制约。他们领取工资,被纳入社保体制内。
武装部队中的军牧按1880年7月8日的法律进行安排。国务院认为,1905年法律在这一问题上的缄默,并不意味着禁止这项由公共资金负责的服务。实际上,在国家军队中有三个军牧团,分别代表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信仰。每一个军牧团都负责其所属教会的军牧工作,并确保军队管理方与宗教当局的合作
[46]。
两个困难阻碍着随驻牧师制度的顺利运行:在医院以及在监狱中,各种教会的随驻牧师数量有所不足;特别是穆斯林的随驻神职人员存在严重短缺。
教士、修士以及宗教神职人员受一般法律的管辖——这些法律适用于法兰西领土上的每一个人。原则上,宗教神职人员并不拥有特殊地位。不过,他们由于自身职责的原因,受到一系列特殊法规的制约,这些法规与其他个体的生活没有关联
[48]。不过,人们并不能说,这是一种特殊地位。
许多个世纪以来,法兰西像大多数国家一样,由教会掌管婚姻和家庭方面的法律。逐渐,在旧政体下,那些制度呈现出世俗化的动向。法国大革命实现了世俗化。今天,在这一领域,法兰西法律与教会法各自独立,但却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我们将研究法兰西民事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与宗教有关的事实。
1. 婚姻的形成
两种法律体系的存在带来了几个困难。拿破仑法典要求,两个希望举行宗教婚礼的人,首先必须在民政官员面前缔结民事婚姻。仅仅举行宗教婚礼,绝不能构成法兰西法律下的有效婚姻,而且,举办该婚礼的宗教神职人员将在刑事上承担法律责任
[50]。不过,在国外以宗教形式庆祝的婚礼,且婚礼遵循所在地的外国法律,会在法国得到承认。在缔结民事婚姻之后,应该考虑宗教事实吗?即便是这样,那也只是间接的。例如,在法兰西法律中,一名教士婚姻的合法性不能被质疑
[51],如果法庭宣布这样的婚姻无效,不会因为教会的禁令,而是因为就个人的根本品质而言的某种过失,即该教士隐瞒了他在教会中的身份。进而言之,一位已离婚人士的再婚可以被宣告无效,不是因为天主教会禁止再婚,而是因为其中一方隐瞒了他或她作为离婚人士的身份,这可作为一种个人根本品质上的过失,其前提是,只要婚姻的另一方能证明,如果这样的事实被知晓,会成为婚姻中的障碍
[52]。再举一个例子:当丈夫或妻子并非法国人时,法官们将应用他们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其婚姻的基本合法性;宗教因素也许会被考虑在内,但其作为该外国法律的要素,而非简单地作为“宗派性的法规”来考虑。不过,有些问题(例如,禁止与另一个宗教的人士结婚)有时会以“公共秩序”为由,不予理睬。
[53]
2. 婚姻的解除
关于离婚,法兰西法律做出了完整的规定,并且,在立法中已经历许多年的发展
[54]。目前,它由1975年7月11日的法律管辖,该法律不考虑宗教法规。两种法律系统各有其固有的领域。民事上的离婚由国家机关认定,且只具备民事后果;教会法规所认定的婚姻无效,对婚姻的民事上可能的无效没有任何影响。不过,宗教因素在世俗法庭中仍可具备一定的相关性:
如果婚姻中的一方拒绝举办宗教婚礼,而在民事婚礼之前,他(她)已同意该宗教婚礼,那么,这是一项严重的错误行为,可以据此离婚。法院注意到,这是违反承诺,并冒犯了受到伤害一方的宗教信仰。
假使经过多年的共同生活,妻子不再履行宗教誓言,这是一项针对丈夫的严重的错,依据妻子的严重错误,丈夫可获准离婚
[55]。
一般而言,法庭拒绝给予离婚许可时,并不考虑天主教会的立场;但是,法庭已虑及如下事实,离婚会违背配偶的意愿,尤其对一个特别投入其教会的天主教徒来说,考虑到天主教信仰关于婚姻不可解散的教义,离婚可能会带来“异常的艰辛”。法官将会应用《民法典》第240条中的“艰辛条款”(hardship clause)。
[56]
民事法官发现,与允许离婚和再婚的宗教打交道更容易,例如犹太教。在犹太教信仰中,丈夫当着拉比的面出具休书(
gett),妻子即被休掉,且妻子再婚可以举行宗教仪式。当民事法官宣布一项民事婚姻的解除时,可以考虑丈夫拒绝出具休书这一因素。他可以命令这位丈夫做出赔偿以补偿妻子。但是,法官没有任何权力要求这位丈夫做出切实的宗教性行动。
[57]
3. 家庭的内部构成(internal organization)
关于家庭的内部构成,法官也会注意到某些宗教因素。他会留意良心自由的原则,允许配偶在婚姻期间改换宗教或宗教礼仪,以避免出现某种宗教狂热,以致会忽略基本婚姻责任。因此,尽管追随某个教派(sect)的行为本身并不是法官要反对的一件事情,但它会导致配偶某一方的“严重过失”。
孩子的宗教教育有可能导致夫妻之间的意见不合
[58]。父母应该一起协商,选择他们将提供何种教育(《民法典》第371条第2款)。一旦选定,法庭将尊重该选择。在离婚的案例中,或是在父母间因为此问题存在意见冲突时,法官将会支持先前所达成的协议中的做法
[59]。此外,法兰西还有义务遵守1989年11月29日的《儿童权利纽约公约》,并且也必须将儿童的辨别能力考虑在内
[60]。
这就是说,家庭法经常要将宗教因素考虑进来,但是,宗教因素被立法者提及的情况少之又少。因此,这是一个案例法的问题,必须基于每一案例的各不相同的事实,谨慎行事。法官不会适用教会法规(canonical rules),但是会留意教会法规对各方之间的“世俗”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
十二、参考文献
基本文献:
Messmer Fr./Prélot P.-H./Woehrling J.-M. (eds.), Traité de droit français des religions, Paris,
LITEC, 2003, 1317 p.
其他资料:
Basdevant-Gaudemet B., Le jeu concordataire dans la France du XIX° siècle, Paris, P.U.F., 1988,
289 p.
Basdevant-Gaudemet B./Messner Fr. (eds.), Les origines historiques du statut des confessions
religieuses dans les pays de l’Union europeenne, Paris, PUF, coll. Histoire, 1999.
Basdevant-Gaudemet B., “Droit et religions en Franc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1998, p. 23-55, reproduits dans: La religion en droit comparé a l’aube du XXI° siècle, (ed.
Caparros), Bruylant, Bruxelles, 2000, p. 123-164.
Bauberot J., Histoire de la laïcité français, Paris, PUF, que sais-je ?, 2000, 128 p.
Bauberot J., Vers un norveau pacte laïque, 1990.
Berlingo S. (ed.), Code européen, Droit et Religions, T.I, Union européenne; les pays de la
Méditerranée, Milan, Giuffré, 2000 (p. 153-273 sur la France).
Boyer A., Le droit des religions en France, Paris, P.U.F., 1993, 260 p.
Durand J.P., in Durand, Echappé, Vernay, Valdrini, le droit canonique, Paris, Dalloz, 1989, 747 p.
Jeuffroy B./Tricard F. (eds.), Liberte religieuse et régimes des cultes en droit français, Textes,
Pratique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 Paris, cerf, 1996, 1242 p.
Kerleveo J., L’Église catholique en régime français de séparation, 3 vol. Paris, Desclé, 1962.
Mayeur J.M., La Séparation des Églises et de l’État, Paris, ed. Ouvrières, 1991, 188 p.
Messner F. (ed.), Les “sectes” et le droit en France, Paris, PUF, 1999.
Poulat E., La solution laique et ses problèmes, Berg international, 1997, 229 p.
Prelot P.-H., “Chronique de droit français des religions”, dans chaque numéro de la Revue
européenne des relations religions États, Leuven, Peeters.
Robert J./Duffar J., Droits de l’homme et libertés fondamentales, Paris, Montchrestien, 7°éd.,
1999, 855 p.
载自《欧盟的国家与教会》,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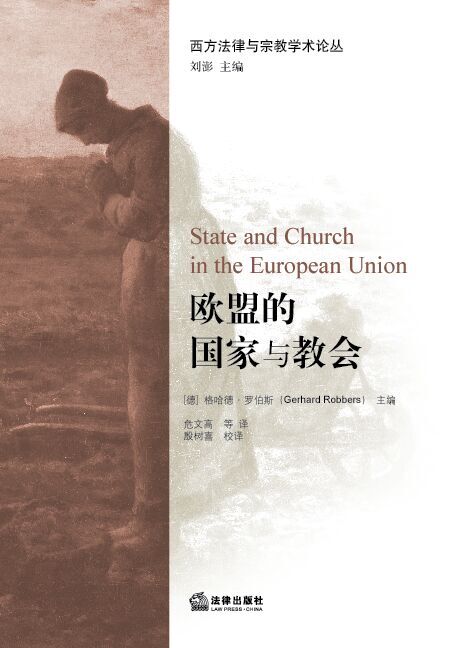
[1] 几乎80%的法国人声称他们自己是天主教徒,尽管经常参加礼拜天弥撒的人只有不到15%。
[2] 第一条确保宗教的公共活动“符合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是政府认为——为了公共和平——所必需的”。宗教的界限由宗教当局与国家当局通过协议重新确定。主教和堂区内教士的薪水由国家资金付给。那些未被放弃、仍有礼拜需求的教堂,留给主教们支配(国务院the
Conseil d’État后来决定哪些属于国家财产,哪些属于教团财产)。
[3] “序言”明确提及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并提及1946年《宪法》序言中对“信仰自由”的保证。第二条规定:法兰西是“……一个世俗(性质的)共和国……确保其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无论其出身、种族、宗教的不同。共和国尊重所有信仰。”
[4] 第一条:“共和国确保良心自由。她保证宗教活动自由仅受到如下所列的公共秩序之利益的限制”。第二条:“共和国不承认、资助、支持任何宗教……然而,在(国家和公共实体的)这些预算中,可以出现与教士服务相关的开销,这些服务被设计出来,以便确保公共机构中的宗教活动自由,例如中学、学院、学校、福利院(nursing homes)、避难所和监狱……”
[6] 1901年7月1日的法律,目前仍保持有效,该法奠定了结社——所有人为了非盈利目标而共享知识或行动——自由的原则。即便没有具体列明其为人所知的目标,结社仍然可以是合乎法律的。经由在府(或厅)保存其成文规章,并获得法律能力,社团得以产生;它可以被法令确认为具备“公共的效用”。一个被如此确认的社团,可以——在相应程度上,以及,以每一个案中法令所许可者为条件得到拨款。但同一法律也包含不利的、非常限制宗教团体的规则:第13条第三款规定“未经一项法律授权,宗教团体不可以成立,这项授权须明确说明为该宗教团体之活动而设定的条件”。
[7] 这一规定被1908年4月的法律以一种有利于教会的方式修正,它允许地方当局承担他们所拥有的教会建筑物的维修成本。
[8] Les congrégations et 1'Etat [The religious orders and the State], ed.,
J.P. Durand,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2, 139 p.;
J.P. Durand, Les congrégations religieuses: droit canonique et droit français, [Religious Orders: Canon Law and French Law] thesi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Paris XI and ICP, Paris, Cerf, 1999, 3.
[10] B. Basdevant-Gaudé
met et F. Messmer, “Leséstablissments de santéet les institutions d’assistance confessionnels en France ”, Revue de Droit canonique, tome 52/1, 2002, p. 187-213; reproduits dans Les Établissements d’assistance, 1’État, lesÉglises et la société,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Church-State Research, Guiffré, Molano, 2003, p. 73-99.
[11] 参见paper presented by
B. Basdevant-Gaudemet, “les activities d’assistance”, 8
th Congress of Canon Law, Lublin, September 1993.
[12] Secours Catholique, the CCFD 等等,(这些机构)被公共当局完全承认为教会实体,拥有“明显特征”以及独特目标,但是,它们在其各种不同的活动中,都得以与公共当局合作,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国际的。
[13] A. Bamberg, Hopital et Eglises [Hospital and Churches], cerdic, Strasbourg, 1987, 408 p.
[14] A. Bamberg, Hopital et Eglises [Hospital and Churches], Strasbourg, 1987, 408 p. 法律情形方面的多样性,并未阻止国家承认和尊重其“明显特征”;亦未阻止国家认可特定活动是——或者不是——在特定组织内实施的。特别的一点,主动终止妊娠可能会被禁止。教会关注(要求)该“明显特征”被写进书面规章中,对此,法官在任何民事诉讼中都将予以尊重。
[15] 参见下文,第六部分(原文如此,应为第七部分,译者注):劳动法与教会。
[16] J.-L. Vallens (ed.), Le guide du droit local; le droit applicable en Alsace et en Moselle de AàZ, Paris, Économica, 1997.
[17] F. Messner, P.-H. Pré
lot, J.-M. Woehrling, Traité de troit français des religions, Paris, Litec, 2003, p. 835-838.
[18] 参见
N. Fontaine, La liberte, d’enseignement, guide juridique de l’enseignement associé à 1’Etat par le contract, [教育自由:与国家契约之下的关于教育的法律] 3
rd ed. Paris, UNAPEC, 1980, 665 p.
[19] (C.C. 23 Novermber 1977, A.J.D.A. 1978, p. 565, note Rivero; C.C. 18 January 1985, R.F.D.A. 1985, 5, p. 633, art. Delvolve). 同一法庭认为,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享有一种宪法性的地位(C.C. 16 July 1971)。
[20] 确保教育自由的主要法律:初等教育,
loi Guizot,1833年6月28日(1882年3月28日和1886年10月30日的法律均涉及公立初等学校中的世俗主义);中等教育,
loi Falloux,1850年3月15日;高等教育,
loi Dupanloup,1875年7月12日;技术教育,
loi Estier,1919年7月23日。
[21] 1806年5月10日的法律创设了帝国大学(the Imperial University),将教育垄断地位留给了国家。在这种公共教育服务的运转中,教会起到了部分作用,但是,处于国家权威的控制之下。(在那时)由私人动议而创立的自由(教育)部门,并不拥有一席之地。
[22] 即便是在第四共和国统治下,通过
lois Marie and Baranger,国家仍给予私立教育机构一定的承认,以及某些物质上的好处。
[23] 这些合同有两种类型:“简单合同”,准许国家直接付工资给职员;以及“协会合同”,这类合同更为普遍,在这种合同下,职员由国家付工资,并由地方当局提供一定的补助,与给予公立学校的补助相同,以此帮助学校的运转。这一制度较为复杂;国家的补助金将用于支付学校成本中或多或少的部分,取决于该校教育的水平或层次。这种复杂性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近来,某些改革措施正在被酝酿中,但尚未被接纳。
[24] J.M. Swerry, Les aumoneries catholiques dans 1’enseignement public, [The Catholic chaplaincies in public education], thesi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Paris XI, 1990, ed. cerf, 439 p., 1995.
[25]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争论:在某些特定的地区,星期六的课程被换到了星期三,以便周末安排家庭活动,对此,主教们对此予以批评。
[26] P.H. Prelot, Naissanc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libre, la loi du 12 juillet 1975, [The birth of free higher education; the law of 12 July 1875], Paris, P.U.F., 1987, p. 139; [same author] Les établissements prives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s,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establishments], thesis,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Paris II, L.G.D.J., 1989.
[27] P. Coulombel, “Le droit privé français devant le fait religieux depuis la séparation de l’Eglise et de l’Etat”, [French private law as to religion since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Rev. trim. dt civ., 1956, p. 1-54.
[28] 目前,有一些正在运行的天主教学院(那些在巴黎、里尔、昂热、图卢兹以及里昂的学院),它们囊括了通往高水平学术的主要院校。这些学院受到源自私人的广泛的资助,包括学生的缴费;但它们也接受来自国家和地方当局的补助金,尽管这并非法律所要求。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情形非常特殊。1902年,经教廷与德国之间的公约,创设了一间神学院。1919年以后,该神学院延续下来,它颁发国家文凭,同时,该文凭也属于宗座颁发(或认可)的毕业证书。
[29] 参见论文:
L. De Fleurquin, “L’Eglise et jes médias”, [The Church and the Media] 8
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anon Law, Lublin, September 1993.
[30] 1933年,当广播服务被国有化时,所有宗教广播都按照世俗主义原则被停止。有些宗教节目很快又被恢复,但是,只是在1944年以后,宗教广播才获得良好的地位。
[31] N. Guinezames, “L’Église et le droit du travail”, Les Églises et le droit du travail dans les pays de 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Milan-Madrid, Giuffrè, 1993, p. 83-103.; J. SAVATIER, “L’animateur pastoral selon le droit du travail”, l’année canonique, t.35, 1992, p. 29-43; G. DOLE, Les professions ecclésiastiques, fiction juridique et réalité sociale, Paris, LGDJ, 1987, 590 p.; Idem, La liberté d’opinion et de conscience en droit comparé du travail; Union europeenne t.1 : Droit européen et droit français, Paris, LGDJ, 1987, 256 p.
[32] 但是,我们应该提及abbé Bouteyre这一著名案例,C.E. 1912年5月10日;国务院判定,这一点是正确的,即教会人士应该被排除在公立中学教师资格的竞争之外。在解释这项决定时,有两点应该被注意到:这是一个公共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关于雇佣的普通法律的问题;以及,该决定是在第三共和国——反教权主义高峰——时期做出的。人们好奇,如果这一问题出现在今天,国务院是否会坚持它的看法。
[33] J.P. Durand, in Valdrini, Durand, Echappé, Vernay: Le droit canonique, précis Dalloz, Paris, 1989, p. 622.
[34] 这里不考虑荣誉助理(honorary assistants)的情形,对荣誉助理,大多数劳动法规不适用。
[35] C. Cass. Ass. Plén. 19 May 1978, D. 1978, p. 541, concl. Schmelck, n.Ph. Ardant. 该项裁决业已陈旧。教会(现在)避免将这类案件入禀法庭,因为法庭在这类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在发生改变;“Les motifs de licenciement dans les entreprises de tendance”, synthèse du colloque du centre Droit et Societies religieuses, par
E. Hirsoux, l’annee canonique, 39, 1977, p. 151-174.
[36] Fr. Messner, Le financement des Eglises, [The Financing of Churches] Strasbourg, cerdic, 1984, 259 p.
[37] 这可以采取两种形式:(1)常规奉献,由每一个体交给其所属的堂区协会,没有确定的数额规定;(2)星期日礼拜时所做的奉献。
[38] 教会所收集者,系信徒的自愿贡献;实际上,那些经常出席教会仪式的天主教徒,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做奉献,这似乎只能算是一种不牢靠的收入,尽管看上去它能够支付教区神职人员的工资。弥撒之外的资金募集活动,使收入得以增加。
[39] J. Gueydan, X. Delsol, P. Desjonqueres, Cultes et religions, impôts et charge sociales, [Churches and religious groups: taxation and social charges], Paris, LGDJ, 1991, 270 p.
[41] 1961年7月29日的
loi de finance rectificative(第11条)准许各省和市镇做出这种担保;国家通过财政部,可以做出同样的担保。
[42] J.P. Durand, “Chronique de droit civil ecclésiastique”, l’année canonique, 1988, p. 443-462; 税务扣减额度的增加,允许并使得“教会奉献”的扣减成为可能。
[43] 许多穆斯林的“宗教协会”处于这一地位,这些协会的目标并不只是礼拜活动,而是也包括建设古兰经学校、图书馆,等等,它们一般与清真寺相伴随。这也是许多教会领域中的教育实体所选择采取的法律形式。
[45] G. Dole, Les professions ecclésiastiques, op. cit. p. 312.
[46] 这些军牧团中的人员,可被区分为三个类型:(1)部队军牧(the military chaplains)——恰如其名——由部长任命,其职业生涯与官员并无二致;(2)文职身份的军牧(chaplains engaged in a civil capacity),他们拥有一份雇佣合同;(3)志愿军牧(voluntary chaplains),没有工资,但享有国家的保险,以防其在工作出现事故。
[47] J. Kerleveo, l’Eglise catholique en régime francais de séparation, [The Catholic Church under the French régime of séparation] T.III, Le prêtre catholique en droit francais, [Catholic Priests in French Law] ed. Déscle, Paris, 1962;
P. Barbier, “Le ministre du culte peut-il voir sa responsabilité civile engagée a l’occasion des actes qu’il accomplit dans l’exercice de son ministerè”, [Civil liability of ministers of religion for acts involved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calling], l’annèe canonique, 1987, p. 235-256.
[48] 特别针对宗教神职人员的这些权利和义务,可举出如下例证:1)有些职业——数量上很少——与宗教神职人员的地位不相兼容。1882、1886和1904年的法律,渐次禁止教士在小学任教,这一禁令或许扩充到了中等教育(参见上文,第五部分)。2)《民法》第909条禁止宗教神职人员从临终生病期间曾接受其精神照顾的病人手中接受礼物或遗产。3)某些牧养功能的实施,必须遵照世俗法律的规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禁止宗教神职人员在民事仪式前举办宗教性的婚礼;未经具备民政地位的官员发放行政当局的许可,不得举行葬礼,而民政官员在未见到医生签发的死亡证明前,亦不得采取行动;未经相关利益方同意(或在涉及未成年人时,未经具备父母威权者同意),禁止举行圣事(例如洗礼);这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良心自由(参见Liege, 1909年5月5日,D.P. II.2.364;一位祖母在未经孩子的丧偶的父亲的同意下,为孩子举行了洗礼,被判赔付象征性的损害)。4)当过失是由宗教神职人员犯下时,某些特定的惩罚会被加重。5)保守职业秘密(不限于信仰方面)的责任,使得宗教神职人员可以——就那些因履行职务而知道的事情——拒绝作证。等等。
[49] G. Cornu, Droit civil, la famille, Domat 2003;
J. Carbonnier, Droit civil, la famille, Paris, Montchretien, 1999, 20°éd.;
Malaurie etAynes, Droit civil, la famille, Paris, Cujas, 1998, 6°éd.;
H. Gaudemet-Tallon, v° “famille”, Répertoire Dalloz, 1997; “Divorce et nullité de marriage, colloque de droit canonique et de droit civil”, actes du colloque de Poitiers, avril 1989; l’annee canoqique, t. 32, 1989, p. 13-195;
Y. Geraldy, La religion en droit privé, these droit Limoges, 1978; numerous articles in the Revue de Droit Canonique, Strasbourg.
[50] Art. 199 and 200 C. pen. Cf.
T. Revet, “De l’ordre des celebrations civiles et religieuses du marriages”, [Of the order of celebration of civil and religious marriage], la Semaine Juridique, G. no. 49, 1987, 3309, p. 1-8.
[51] 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已被接纳,它也是目前法院的立场;1905年的法律对该问题没有影响(C.Cass. civ. 1888年1月25日)。
[52] T.G.I. Le Mans, 7 December. 1981, J.C.P. 1986, 20573.
[53] H. Gaudemet-Tallon, La desunion du coupl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receuil des cours, acade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91, 1, 279 p.; 关于宗教问题,见179-273页。
[54] 1792年9月20日的法律首次引入了离婚,视其为个体自由本质上的必然后果;其后的改革减少了(离婚的)可供选择的理由。在1804年的《民法》中,仍然允许离婚,但男人比女人更容易获准离婚。在1816年的复辟时期,离婚被废除。最后,1884年7月27日的法律the
loi Naquet在法国重新确立了离婚(的合法性)。
[55] C. A. Amiens, 3 March 1975, D.S. 1975, p. 706.
[56] Civ., 2, 23 October 1991, D. 1993, p. 193, 1° esp. n. Villaceque. 不过,一种最近的观点是,在现代社会的环境下,即便是一个已婚的虔敬的天主教信徒,也应该接受(或被许可)离婚。
[57] P. Barbier, “Le problème du Gueth”, G.P. 1987, doct. p. 485 e, , t C. Cass. 15 juin 1988, Bull. Civ. II, no. 146; C. Cass. 21 November 1990, D. 1991, 434, n. E. Agostini;
H. Gaudemet-Tallon, op. cit. p. 248-253.
[58] Cl. Castellan, L’education de l’enfant, puissance, paternelle en droit canonique et autorité parentale en droit français, Thèse, droit, Paris VI et ICP, 2001. 长期以来,在混合婚姻(指跨宗教婚姻,译者注)的案例中,教会要求,非天主教信徒的丈夫或妻子要承诺允许天主教信徒的配偶以天主教信仰抚育孩子。在教会眼中,这样一项协议是合法的,但在民事法庭上并非如此。不过,民事法官也不能无视它,法官可以裁定,存在着对先前协议的违反,而无需考虑该协议的内容之类的问题。
[59] Paris, 6 April 1967, J.C.P. 1967, II, 15100.
[60] Cass. Civ. 1° 11 June 1991, D. 1991, 521 n.
Malauri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